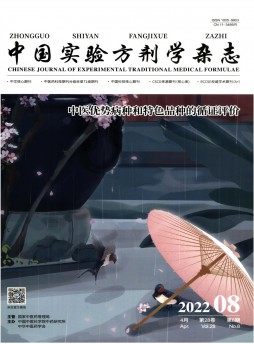方劑學的臨床研究方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方劑學的臨床研究方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西中醫藥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關鍵詞:
方劑學;研究方法;配伍規律
李海延[1]在論述中醫臨床醫學面臨的挑戰及策略中提出:臨床基礎學科成立后雖然對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有利的影響,但也明顯地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歸納起來說,主要面臨三方面的困境。其一,《傷寒論》、《金匿要略》、《溫病學》的合并是教育規劃的結果,合并之前應該進行過科學的論證。但到目前為止,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是“三家”分而行之,基本與合并之前無太大變化。所以,遠遠沒有達到產生“合力”的效果。筆者認為方劑學是中醫學的主干基礎課程之一,是中醫基礎與臨床之間的橋梁,所以在此方向著力,可以解決現在中醫臨床面臨的諸多問題。具體來說,方劑學理論能夠指導中醫臨床治療,而中醫臨床的整理和改進能補充方劑學的內容,同時臨床實踐的進行又能印證方劑學理論的實用性。歸根結底,我們對于方劑學的研究就是為了提高醫生在臨證時的專業水平以及對疾病把控的穩定性。方劑學回歸臨床是方劑學研究最重要的也是最直觀的方式,以臨床療效和方劑學理論的相互輝映,相互連接,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調整方劑的藥物配伍和劑量,使臨床療效提高的同時增加和豐富方劑學的應用范圍和應用信心。研究方劑學的方法和角度有多種,從研究方法來劃分,主要有基礎方劑學、實驗方劑學、網絡方劑學、臨床方劑學;從研究內容來劃分,主要有配伍規律、臨床應用、煎服方法與口感研究、方劑與體質辨證等。本文現就方劑學的臨床研究方法作此論述。
1方劑中藥物配伍的研究
方劑學配伍的研究參考因素有多種,目前我們在臨床中運用和研究最頻繁的是以下幾種因素。
1.1藥味加減的研究
方劑的選擇應在對患者準確辨證以后運用對癥合理的方劑,在選擇方劑以后根據不同的病理偏性或藥物的作用范圍選擇藥味加減。方劑中藥物加減的靈活變化可以擴大本方劑的適用范圍,也可以對一些比較重要的特殊兼癥加以針對治療。如逍遙散本是治療肝郁血虛脾弱證,適應證為兩脅作痛,頭痛目眩,口燥咽干,神疲食少,或月經不調,乳房脹痛,脈弦而虛者,而院建生[2]將臨床常見的神經緊張性頭痛分為肝郁陽抗、痰濁中阻,氣虛虧虛三種證型,將逍遙散藥味的加減化裁運用于臨床取得滿意療效。肝郁陽亢證用逍遙散加天麻、鉤藤、桑寄生、杜仲,壯腎水以養肝木,使得逍遙散在疏肝的同時而不傷肝陰;痰濁中阻證時予逍遙散加半夏、白術、天麻等以祛痰止眩;氣血不足時用逍遙散加川芎、熟地黃等滋補精血以柔肝。又如邵正泰等[3]在治療中氣不足引起的濁陰不降(癃閉)時,予補中益氣湯加肉桂、黃柏以助腎氣化水,以增強補中益氣湯在下焦助氣化的能力,以達功效。由此可見方劑中藥味的加減可以擴大方劑的治療范圍。
1.2藥物比例的研究
在選定方劑以后,方劑中藥物劑量之間比例的改變會影響方劑的使用范圍和使用功效。桂枝湯在調和營衛時古今醫案中的用量與原方基本一致,其中桂枝和白芍的比例是1∶1,而在治療內傷發熱、心悸失眠等證屬陰不足時桂枝與白芍的比則可出現1∶2或者1∶3[4]。再以當歸補血湯為例,文獻記載的當歸∶黃芪之比除1∶5外,還有1∶6(《外科理例》),1∶4(《醫學心悟》、《時方歌括》),1∶3(《醫部全錄》),1∶2(《血證論》),2∶5(《東醫寶鑒》),3∶8(《醫學入門》),3∶10(《女科撮要》)等比例。而在現代研究關于當歸與黃芪的比例對療效的影響也有所體現,如李儀奎等[5]通過動物實驗研究當歸及黃芪單獨用藥和不同配比下的差異,結果顯示單用或聯合配伍均有補血作用,而當歸與黃芪的比例為1∶5時效果最佳。張英華等[6]觀察小鼠造血紅細胞的變化,分析當歸與黃芪的比例對小鼠的含藥血清的影響,結果顯示黃芪的比例較大時藥效強度較高,即當歸與黃芪的比例為1∶5時效果優于1∶1。孟翔宇等[7]考察了麻黃與甘草藥對配伍后化學成分的變化,實驗結果表明,麻黃與甘草不同比例配伍后,麻黃中麻黃類生物堿的溶出率與麻黃單煎液相比明顯減少,其溶出率與甘草在藥對中所占的比例有關,甘草比例越大,麻黃類生物堿的溶出率越小;麻黃與甘草配伍后,甘草中各有效成分的溶出率與甘草單煎液相比也明顯減少,隨著甘草的量增加,麻黃對甘草的煎出量影響越大。綜上可見,方劑中藥物不同劑量比例各有自己的作用優勢。
1.3藥物劑量加減的研究
劑量是藥性的基礎,也是決定藥物配伍后發生藥效、藥性變化的重要因素。中醫臨床治療要依據辨證施治的原則遣藥組方,確立藥味多少,定其用量大小。因病有輕重之分、表里之別、虛實之不同,亦有上、中、下三焦之屬,只有在辨證準確的基礎上確定藥量大小,才能把握治療效果。方中藥必適量,過大過小對治療都有影響,如果病重藥輕則杯水車薪,不足以勝病,病輕藥重更會耗傷正氣或造成中毒,甚至置人于死地,所以正確掌握中藥的用量至關重要。徐靈胎曰:“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8]君臣佐使是方劑藥物配伍的主要規則。每個方劑中都有一味君藥,其劑量舉足輕重,若將方劑中藥物的劑量稍加變化,則會影響整個方劑的作用方向。這是因為藥物的功效會因為劑量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如紅花,《本經逢原》中提到:“少則養血,多則行血,過用使人血行不止。”[9]而黃芪小量升血壓,大量則降血壓,氣虛難汗者用之可汗出,表虛多汗者用之可汗止[10]。綜上,只要方劑藥物配伍得當,不但重劑可以起沉疴,輕劑也可以療頑疾。關于藥量的大小,一是要考慮到藥物的多向調節功效,二是要病例產物聚集停留的部位,三是必須符合正邪虛實變化格局[11]。
2方藥煎煮方法與改善口感的研究
依從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對醫療或健康建議的遵從程度,包括用藥、膳食、生活方式等方面。研究顯示,以服用中藥湯劑過程中出現“不合理現象的個數”作為評價指標,服用中藥湯劑總體依從性與自覺療效呈顯著相關[12]。即患者的依從性對中藥的治療效果具有明顯的影響。筆者經臨床觀察發現患者服用中藥湯劑不能依從的主要因素,一是中藥的湯劑煎煮復雜,二是口感不適。給小兒或者脾胃虛弱的老年患者開處方時特別應考慮方藥的口感。改善方藥方法是將方中次要功效且口味偏差的藥物以相似功效且味道較好的藥物更換,必要時可減少藥物劑量或直接刪除。如臨床上使用仙方活命飲治療瘡瘍腫毒初起的陽熱實證時可將沒藥改為檀香、延胡索以改善口感,促進患者服藥。在現代的中成藥研究中也能獲得-些啟示:在制作好的原中藥藥品中常需加矯味劑以在一定程度上掩蓋與改善制劑的不良氣味,便于內服,尤其受兒童患者的歡迎。目前國內常用的矯味劑有:甜味劑、芳香劑、膠漿齊口和泡騰劑[13]。目前改善口感的主要方法有改進中藥劑型及給藥方法、開展代煎藥、采用中藥顆粒劑代替傳統湯劑給藥等。國家已開始重視中醫藥事業并加強對中藥現代化的研究工作,逐漸改變中藥傳統用藥習慣,對中藥有效成分進行科學分離、提取,并根據中藥有效成分制成注射劑、膠囊劑、顆粒劑及口服液等劑型,以方便各年齡段、各類人群使用[14]。
3方劑與體質辨證關系的研究
《黃帝內經》較早地認識到體質問題,認為體質的形成受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共同影響。先天稟賦是構建人體體質的第一塊基石,而后天因素諸如地理環境、社會因素、飲食勞逸、情志狀態、疾病針藥等也影響體質的形成與變化[15]。葉天士在臨證中,對體質甚為重視。《臨證指南醫案》中記載“平素體質,不可不論”,“診之大法,先明體質強弱,肌色蒼嫩,更詢起居致病因由”等言論[16],可見葉天士對體質的重視程度。在臨床選用方劑時注重體質辨證可使得選方的方向更為明確,臨床的思路更為清晰。在臨床上根據不同體質的患者確定不同側重的治法,選擇相關方劑進行治療。中西醫在體質的分類上有多種方法,而中醫普遍將體質分為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陰虛質、痰濕質、濕熱質、瘀血質、氣郁質、特享質等9種基本類型[17]。這種體質分類方法從客觀可見的方藥運用指征以及常見多發的癥狀體征入手,有利于中醫藥客觀化研究和個體化治療。如臨床上對于肥胖患者即痰濕體質,不管患何病,始終適當加入化濕類中藥,可提高療效;對于體瘦患者即陰虛體質,治療時避免辛燥藥物,始終注意固護陰津,可防熱化[18]。在臨床選方時應得到啟示,在患者體質偏性的前提下我們在選擇方劑時應注意顧護正氣與驅邪外出相結合,以達到提高治療質量的目的。
4結語
中醫在臨床上,理、法、方、藥的環環相扣,有其特殊的思維方式和邏輯線路。對疾病進行診斷和立法處方共同構成了中醫臨床思維的全過程[19]。而一首方劑的確立,要經據證立法、審證求因、擇藥定量、合理配伍等一系列抽象的思維過程,因而中醫方劑學是中醫學辨證論治精髓的集中體現。近十余年來,隨著對方劑配伍科學內涵的逐步揭示,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方劑學研究熱潮。規律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方劑學臨床研究的任務就是盡可能的揭示方劑中藥物的配伍規律,通過探索藥物的加減規律、藥物的劑量規律、藥物的比例規律、煎煮方法以及口感的控制等以用于指導醫生的臨床操作[20]。所以探求方劑學的配伍規律對于在更高的層次上認識方劑的配伍和指導臨床用藥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通過方劑學的臨床研究,可以讓我們更直接直觀地研究方劑學。重視臨床、勤于臨床,是我們推動方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李海延.中醫臨床醫學面臨的挑戰及策略[J].中醫中藥,2015,15(30):176.
[2]院建生.逍遙散加減辨證治療緊張性頭痛[J].實用中西醫結合臨床.2014,1(14):76-77.
[3]邵正泰,邵高魁,郭長峨.補中益氣湯治驗舉偶[J].河南中醫藥學刊,1994,9(4):36-37.
[4]袁世清.張琦.高燕.桂枝湯用藥規律文獻研究[J].中醫雜志,2015,56(21):1881-1882.
[5]李儀奎,徐軍,張曉晨,等.黃芪當歸藥對配伍的藥理作用研究[J].中藥藥理與臨床,1992,8(2):1-4.
[6]張英華,武桂蘭,姜廷良.當歸補血湯及其含藥血清對小鼠紅系造血祖細胞克隆的影響[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1999,5(4):33-36.
[7]孟翔宇,皮子鳳,宋鳳瑞,等.麻黃甘草藥對配伍前后主要藥效成分及抗炎活性的變化[J].應用化學,2009,26(7):801-806.
[8]郝香梅.大劑量五靈脂的臨床應用[J].山西中醫,1993,9(6):39.
[9]李惠紅.小劑量黃芪升血壓,大劑量黃芪降血壓[J].中國中醫藥雜志,2004,2(5):272-273.
[10]張必祺.中藥黃芪及其活性部位對血管舒縮功能作用的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6.
[11]趙慧輝,劉養清,侯娜.中藥用量探微[J].光明中醫,2005,20(6):2-4.
[12]張露蓉,江國榮,宋如裙,等.142例護士服用中藥湯劑的總體依從性與療效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藥房,2012,23(3):265-267.
[13]周進東,羅興洪,劉武.中藥口服液的純化與口感探討[J].中醫藥研究,2001,17(3):42-43.
[14]杜國安,患者用藥非依從性的原因分析及預防[J].時珍國醫國藥,2004,15(8):57-58.
[15]郝靜,張慶祥,體質辨證的臨證舉隅[J].山東中醫雜志,2014.33(8):689.
[16]包海燕,葉天士體質思想淺析[J].中醫藥導報,2011,17(1):34-36.
[17]姚潔瓊,李宜放,9種基本中醫體質類型與方證體質的聯系[J].國醫論壇,2015,30(5):58.
[18]畢蓮,吳光炯教授體質辨證經驗介紹[J].貴陽中醫學院學報,2015,37(1):58-59.
[19]李峰,張麗君.構建中醫臨床思維教育模式[J].中醫教育,2008,27(2):5-7.
[20]樊巧玲,李飛.關于方劑學研究中若干問題的思考[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0.16(1):2-3.
作者:余之民 林江 羅眈 王志威 胡啟洋 單位:廣西中醫藥大學
- 上一篇:宗教中國化發展探析范文
- 下一篇:社區健康管理模式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