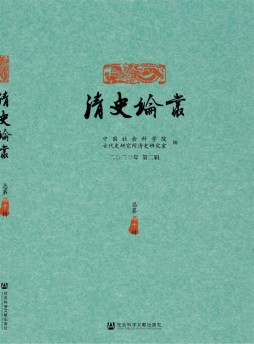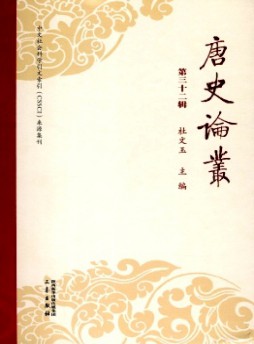史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史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大家都知道,實踐性原則是各科都應遵循的原則,對小學社會課尤為重要,而教材的編排特點又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這是由小學社會課的教學目的所決定的。《九年義務教育社會教學大綱》中規定:“社會課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認識一些常見的社會事物和現象,初步了解一些家鄉的、祖國的、世界的社會常識;從小培養他們正確觀察、認識社會、適應社會生活的初步能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以及法制觀念的啟蒙教育,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那么,如何在社會課教學中根據教材編排的特點,重視實踐性原則,從而達到大綱中規定的教學目的呢?
一、重視社會調查,講求調查實效
翻開社會課教材,我們不難發現,課本中設了“說一說”、“做一做”、“討論”、“活動”等小欄目,其中“活動”這一小欄目中有大部分內容要求學生要深入社會,進行社會小調查。從社會課的編排特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它講究單元教學,但又拘泥于篇章;它啟發學生明理,但重在了解社會,到社會中去實踐。因此,教材在編排上除了設有社會小調查這個小欄目外,還另設了與單元教學內容密切相聯的,要求學生走出課堂進行實地調查的活動課。根據教材內容的編排特點,要求我們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與實踐相結合,安排一定的時間,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有計劃、有組織地積極引導學生參加課本中規定的社會調查等實踐活動,讓學生深入周圍社會,通過親身體驗,具體感知,從而獲得安全的知識,切實達到大綱規定的教學目的。
比如:第一冊教材第三單元“我們周圍的社會生活環境”,根據本單元的教學目的及教學大綱中的有關要求,本單元的教學重點為兩點:(一)、熟悉自己家庭附近的社會生活環境。(二)、結合各行各業人們的生活實際,理解人們之間互相提供服務的關系。本單元共有五課,其中最后一課是活動課《周圍社會小調查》,調查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周圍的社會生活,也是對前四課的總結。調查的內容有:人口、學校、醫院(衛生所)、商店(供銷社)、道路、集貿市場、文化娛樂場所(鄉文化站)等的變化。在教學中,僅憑前四課的課堂教學,很難達到教學目的,而突出單元兩點教學重點勢必就會成為紙上談兵。我們都清楚,每個家庭周圍生活環境是有差別的。所以,只有讓學生結合課堂所學知識,走出課堂,走向社會,進行實地調查,才能進一步地認識家庭周圍生活環境。
社會調查要講求實效,不能流于形式。教師在教學中要按照社會調查的一般步驟有計劃的組織學生。首先,要讓學生明確調查的目的和調查的要求。其次,編寫調查提綱,使學生在調查前做到心中有數。第三,周密組織學生實地調查。第四,認真組織學生總結討論、概括,使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
二、課內外結合,上好觀察課
小學社會課教學大綱確定教學內容的原則之一,就是以認識社會為線索,由近及遠。就范圍來講,從小到大,從知識層次來說由易到難。這就要求我們教師在教學中要重視每一個教學內容,而完成這些教學內容則是為了最終能夠達到讓學生逐步認識社會、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目的。重視實踐,課內外結合,上好觀察課,是達到這個教學目的的有效途徑之一。
第2篇
英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源起一般追溯到1942年的貝弗里奇報告,或是更早的《1911年國民保險法》。下面是編輯老師為大家準備的英國濟貧法演變史。
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救濟法《濟貧法》,源起于14世紀,幾經變革與修正,一直延續到19世紀,在400多年的歷史里作為英國主要且重要的救濟制度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為現代社會保障立法構建了一定基礎。對濟貧法史的演進過程進行分析,可以充分挖掘社會保障與救濟制度背后的社會基本經濟形態的決定性作用,探求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科學規律。對比今日,更可以感受到歷史微妙地影響著今天。如英國社會保障專家Mesher所評論:雖然《濟貧法》的具體形式和機制已經被廢除,但隱含在濟貧法中的觀念與政策仍然深植于現行的法律和實踐中。
1601年的《伊麗莎白濟貧法》和1843年《濟貧法修正案》作為濟貧法中重兩部具有重要意義的立法前者具有發端意義而后者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通常被稱之為舊濟貧法與新濟貧法以區分其不同。本文也以這兩部法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兩部法律的差異出發,試圖探究英國濟貧法演進背后的社會原因,并重點分析由之引發的立法觀念的轉變。
1601年對《伊麗莎白濟貧法》進行法典化被認為是濟貧法的開端。隨后的《1622年王位繼承法》中部分法規和1722年《定居就業與救濟法》對其具體實施規定做出了修改。《1782年托馬斯吉爾伯特法案》與1795的斯賓漢姆蘭制度也分別做出了為滿足當時社會需求的不同程度的補充與修正。逐漸地,英國形成了以征收濟貧稅、建立濟貧院、實行教區安置為主要內容的一整套濟貧制度。這一時期的《濟貧法》是在封建制度瓦解、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初期的巨大社會變革下產生的,表現出了明顯的被動性、應對性、反人權等性質,體現了出于恩賜(對于教會)與恐懼(對于政府)的立法理念。
編輯老師在此也特別為朋友們編輯整理了英國濟貧法演變史。
第3篇
(一)關于貨幣的起源和本質
唐代對貨幣起源的認識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幣”說(亦稱“貨幣國定說”)。此說在《管子》一書中多處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見于《國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玉起于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這一觀點產生以后影響至巨,幾成定論,成為貨幣起源說上的主流認識。
唐代堅持此說的以張九齡、陸贄、白居易、楊于陵等人為代表。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張九齡在所擬《敕議放私鑄錢》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為錢以通貿易”。[1]德宗貞元十年(794),陸贄在《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中說:“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又說:“錢貨者,官之所為也。”[2]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兇;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3]穆宗長慶元年(821),戶部尚書楊于陵認為,“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通變不倦”。[4]
這些言論從便利商品交換的技術角度及維護政權統治的實際需要出發,來解釋貨幣的起源,認為貨幣乃是帝王賢哲人為設計制造出來的,在認識上是一種“非常膚淺的觀點”,[5]也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看法。它把貨幣的產生解釋為是政治權力和統治利益的產物,從而混淆了貨幣起源與商品交換之間的內在聯系,也進而阻止了對貨幣本質問題的正確認識。這種觀點認為貨幣實際上是人君之權柄,是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一個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貨幣是在商品交換中自發產生的,是用于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質所在。總而言之,貨幣起源論上的膚淺和錯誤,決定了貨幣本質論上的想當然和謬誤。這樣的認識水平,與西漢司馬遷所持“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6]的貨幣自然發生說相比,無疑在正確的認知道路上是相去甚遠的。司馬遷雖未認識到貨幣本身即是一種特殊商品,但他把貨幣的產生與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聯系在一起,認為“龜貝金錢刀布之幣”是“農工商交易”發展的結果,提出了關于貨幣起源的正確的和客觀的觀點。唐代統治階級則僅僅是接受《管子》的成說,并沒有去認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關于貨幣的職能
如所周知,按照的貨幣理論,貨幣具有兩種基本職能:一是價值尺度(價值標準),二是流通手段(交換媒介),其中價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價值尺度為前提,因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價值,貨幣才能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不過,這兩種職能又是統一于一體的。馬克思指出:“一種商品變成貨幣,首先是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換句話說,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是貨幣。”[7]
唐代對貨幣的兩種基本職能有所認識。如杜佑認為,“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于為器為飾,谷帛又苦于荷擔斷裂,唯錢可以貿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認為,“錢之為物,貴以通貨”。[9]楊于陵認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憲宗頒《禁采銀坑戶令采銅助鑄詔》,內云:“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雍,貨當益賤。”[11]穆宗《定錢陌敕》亦云:“泉貨之義,所貴通流。”[12]
這些觀點指出貨幣不僅具有“數”,即價值標準,具有權百貨的職能,而且能夠“貿遷有無”,并“貴在通貨”、“義在通流”,不應蓄藏雍滯,對貨幣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職能的認識明確。不過,需要加以辯明的是,唐代的這些認識并不是來源于對貨幣本身屬性的具體探索和科學研究,而是從貨幣起源上的國定說和貨幣本質上的工具論出發加以推衍而認知的。
從貨幣起源上的國定說出發,唐代統治階級認為,貨幣本是無用之物,即沒有什么價值,貨幣所以具有“數”、具有“權百貨”的價值標準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國家權力的制定。他們認為,貨幣既然由國家制造,那么單位貨幣的價值大小也由國家確定。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論是韓愈在《錢重物輕狀》中所陳解決通貨緊縮之對策第三條,即:“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張國家可以根據需要隨意調整、確定單位貨幣的價值大小。這種被學界稱之為貨幣名目論的價值尺度觀,顯然是直接承繼了《管子》所謂貨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觀點,在認知上也沒有超出西漢晁錯所謂“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無視貨幣作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價值大小,無視貨幣價值的自然屬性,認為貨幣由無用之物變為眾人之寶,決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國家權力的確定,在理論上顯然是錯誤的。
從貨幣本質上的工具論出發,唐代統治階級認為,國家制造貨幣的目的在于調節萬物輕重,疏通商貿,發展封建經濟,鞏固統治秩序。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掌握使用好貨幣這一工具,通過國家權力的推行,使貨幣通流不住,不斷地在商品交易中發揮作用,即所謂“義在通流”,或“泉貨之義,所貴通流”。也就是說,貨幣所以能夠在商品交易中發揮流通手段的職能,關鍵取決于國家權力的行使和推動,亦即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也是由國家權力所賦予的。這樣的認識同樣不是對貨幣流通手段職能自然屬性的認知,在理論上也是錯誤的。
對貨幣基本職能的錯誤認識和錯誤理論,尤其是價值尺度觀上的名目論,在我國封建帝制時代根深蒂固,影響巨大,成為歷朝歷代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理論根據,并在實踐上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屢次造成了嚴重破壞,唐肅宗時期推行的通貨膨脹政策是其顯著事例。
(三)關于貨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