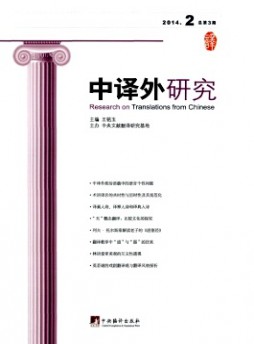描寫(xiě)音樂(lè)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描寫(xiě)音樂(lè)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論文摘要:魏晉時(shí)期是中國(guó)音樂(lè)史上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期。此時(shí)人們對(duì)音樂(lè)的追求,開(kāi)始面向一些新的領(lǐng)域,將注意力轉(zhuǎn)到認(rèn)識(shí)音樂(lè)自身的藝術(shù)特征及其表現(xiàn)方式上來(lái),對(duì)某些理論問(wèn)題的再認(rèn)識(shí),促成了音樂(lè)朝著與過(guò)去不完全相同的方向發(fā)展。這一時(shí)期最重要的兩位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以他們各自的論著闡述了自己的觀點(diǎn)。本文由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美學(xué)產(chǎn)生的背景開(kāi)始,論述這一時(shí)期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他們的主要理論以及對(duì)后世產(chǎn)生的影響。
一、前言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是一個(gè)具有重大意義的轉(zhuǎn)折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的哲學(xué)思想、建安文學(xué)、田園詩(shī)文、書(shū)法繪畫(huà)等都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先秦、兩漢哲學(xué)和美學(xué)所奠定的深厚基礎(chǔ)上又獲得了全面的發(fā)展。像這一時(shí)期這樣高度重視審美與藝術(shù)問(wèn)題,專(zhuān)門(mén)性的著作如此之多,思想如此之豐富多彩,是后世再也不曾見(jiàn)到的。名士一詞最早見(jiàn)于《禮記•月令》:“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此名士,大約相當(dāng)于隱士。不過(guò)隨著秦漢大一統(tǒng)王朝的建立,士子們對(duì)君王和國(guó)家政權(quán)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紛紛干祿求進(jìn),不再隱居不仕,叢而使名士之含義由隱士逐漸向有名氣的人轉(zhuǎn)化。這些名士們曠達(dá)不群,傲然獨(dú)得,高度任性。在他們身上體現(xiàn)出率真脫俗,瀟灑自然的人生態(tài)度和避世超俗,縱情任性,蔑視禮法,我行我素的話(huà)言行風(fēng)范。整個(gè)時(shí)代都張揚(yáng)著一種慷慨奔放的奇麗空氣。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遙遠(yuǎn)的絕響》①中說(shuō)的:“這是一個(gè)真正的亂世。是一個(gè)無(wú)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shí)期’。名士們?yōu)榱怂^的風(fēng)流,風(fēng)度,風(fēng)神,風(fēng)情,風(fēng)姿付出了沉重的代價(jià)。”后世所看到的這些風(fēng)貌特異的魏晉名士,他們的形成卻有著極其復(fù)雜的歷史背景。
二、魏晉音樂(lè)美學(xué)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論
(一)阮籍的《樂(lè)論》及他的美學(xué)思想。
1.《樂(lè)論》及阮籍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
阮籍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集中表現(xiàn)在他的《樂(lè)論》中。阮籍從他的中心論點(diǎn)出發(fā),認(rèn)為最好的音樂(lè)就是“平和之聲”,反對(duì)哀音聲,認(rèn)為音樂(lè)的功用可以“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yuǎn)物來(lái)集。”他之所以斥責(zé)哀音,因?yàn)榘б羰谷饲榫w波動(dòng)變化,使人內(nèi)心的壓抑得到某種認(rèn)同與宣泄。所謂的聲,就是對(duì)人的情感意緒的自然放縱,也即依據(jù)人的感性需要,從而滿(mǎn)足這一需要。阮籍也認(rèn)為音樂(lè)會(huì)隨著時(shí)代的變化而變化,但萬(wàn)變不離其宗,變得只是形式,至于“樂(lè)聲”要達(dá)到的審美的人的心靈趨于寧?kù)o,這樣不悲不喜,靈魂哪兒來(lái)大起大落的震蕩?阮籍這篇短短的《樂(lè)論》,多次提到的“平和”,并把它樹(shù)為音樂(lè)之本,“平和之聲”也是要扼制人的欲望,減弱人的創(chuàng)造激情與活力。阮氏的音樂(lè)思想,客觀上是捆縛阻礙人的激情與生命活力的,是儒家音樂(lè)思想的忠誠(chéng)繼承者。其中透出的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愈來(lái)愈走向了文明的反面,變?yōu)橹舷⑷硕髿⑷说囊魳?lè)創(chuàng)造力的精神桎梏,更可憂(yōu)慮的是這一桎梏隱形地深埋滲透在我們的血脈中,使它化為一種深層意識(shí)而暗暗地規(guī)定制約著我們的現(xiàn)在。
(二)嵇康的《聲無(wú)哀樂(lè)論》及他的美學(xué)思想。
嵇康就說(shuō)于音樂(lè)的言論其實(shí)并不多,一生共留下兩部著作。一部《聲無(wú)哀樂(lè)論》,(以下簡(jiǎn)稱(chēng)《聲論》),另一部《琴賦》。其中《聲論》一書(shū)探討了音樂(lè)美學(xué)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它基本反映出了嵇康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為了清晰起見(jiàn),下面從三個(gè)方面來(lái)分析。
1.音樂(lè)本質(zhì)問(wèn)題。
音樂(lè)的本質(zhì)問(wèn)題是音樂(lè)美學(xué)諸問(wèn)題中具有關(guān)鍵性的論題,對(duì)它的認(rèn)識(shí)將直接影響到對(duì)其它一系列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在研究中,歷來(lái)都為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因?yàn)椋环矫婢佑谝魳?lè)美學(xué)思想大廈的底層,另一方面它是世界觀和音樂(lè)觀相聯(lián)系的紐帶。關(guān)于音樂(lè)本質(zhì),《聲論》認(rèn)為音樂(lè)是一種獨(dú)立的客觀存在,它與人的主觀意志無(wú)關(guān)。作者從兩個(gè)方面對(duì)這一論點(diǎn)進(jìn)行了論述。
(1)音樂(lè)的產(chǎn)生:“夫天地合德,萬(wàn)物資生,寒著代往,五行以成,章為五色,發(fā)為五音”。作者認(rèn)為音樂(lè)是自然的產(chǎn)物,不為人心所生,它相對(duì)于人來(lái)說(shuō),彼此獨(dú)立而存在。
(2)音樂(lè)的自身表現(xiàn):作者認(rèn)為聲音和諧地組織起來(lái),最能感動(dòng)人心。人們賞樂(lè)時(shí),最大的愿望是能夠從音樂(lè)中感受到和諧的存在,而這和諧也正是人們傾注的對(duì)象。它不僅形式上給人的感官帶來(lái)快慰,而且使得人能從心理上獲得平衡。
2.音樂(lè)的審美感受。
音樂(lè)的審美感受問(wèn)題是《聲論》全文探討的中心,作者從“聲無(wú)哀樂(lè)”的論點(diǎn)出發(fā),以自己對(duì)音樂(lè)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為基點(diǎn),闡述了對(duì)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性質(zhì)的理解。涉及到具體問(wèn)題時(shí),得出以下幾種結(jié)論。
(1)音樂(lè)不能喚起人相應(yīng)的情感。
(2)人在聽(tīng)音樂(lè)時(shí)會(huì)有情感出現(xiàn),但各人的體驗(yàn)卻不盡相同。只有和諧的音樂(lè)才能激發(fā)起人的情感。
(3)欣賞者不能與創(chuàng)作者在情感上獲得溝通。
3.音樂(lè)的社會(huì)功用。
《聲論》對(duì)于音樂(lè)的社會(huì)功用問(wèn)題的探討,是圍繞著“移風(fēng)易俗”間題展開(kāi)的。他認(rèn)為音樂(lè)進(jìn)行移風(fēng)易俗依靠的是自身的“和諧”精神。嵇康所認(rèn)為的音樂(lè)“和諧”精神對(duì)于人心的影響,是指人在賞樂(lè)時(shí)能夠獲得性情方面的陶冶。
三、魏晉名士對(duì)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做出的貢獻(xiàn)對(duì)后世的影響
魏晉時(shí)期社會(hu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思想方面發(fā)生的巨大變化,給音樂(lè)的發(fā)展帶來(lái)巨大影響。
漢以來(lái),儒家音樂(lè)思想,對(duì)其音樂(lè)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起了極大的阻礙作用。嵇康音樂(lè)思想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種可悲的局面。他在《聲無(wú)哀樂(lè)論》中,指出音樂(lè)本身并無(wú)哀樂(lè)可言,音樂(lè)中屬于藝術(shù)的因素,同儒家附加上的非音樂(lè)藝術(shù)因素相區(qū)別,他反對(duì)將音樂(lè)同哀樂(lè)混在一起。與此同時(shí),他直接將注意力集中到音樂(lè)藝術(shù)的許多具體方面,對(duì)某些樂(lè)器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特點(diǎn)作了分析比較,究其異同,對(duì)一些樂(lè)曲進(jìn)行了鑒賞,對(duì)有關(guān)音樂(lè)美學(xué)及表演藝術(shù)等理論問(wèn)題有所探討。這種種探討的作法本身就應(yīng)看做是一大進(jìn)步。而阮籍的《樂(lè)論》影響不大的原因在于并沒(méi)有提出一種新的觀點(diǎn),但這不能說(shuō)《樂(lè)論》缺乏研究?jī)r(jià)值。一方面,《樂(lè)論》作為阮籍直接闡述藝術(shù)問(wèn)題的著作,是探究阮籍美學(xué)思想的重要文本;另一方而,雖然《樂(lè)論》所表達(dá)的觀點(diǎn)基本上同儒家傳統(tǒng)樂(lè)論一脈相承,但并不是儒家樂(lè)論的轉(zhuǎn)述,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chǎng)對(duì)儒家樂(lè)論的闡釋發(fā)揮,因而其審關(guān)觀念在思維方式及總體特征上呈現(xiàn)出新的面貌。
注釋?zhuān)孩佟哆b遠(yuǎn)的絕響》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之一。文中主要描寫(xiě)了魏晉時(shí)期兩位名士--阮籍和嵇康,文筆優(yōu)美,意蘊(yùn)深刻。
參考文獻(xiàn):
【1】李澤厚 劉綱紀(jì):《中國(guó)美學(xué)史》安徽文藝出版社
【2】修海林 羅小平:《音樂(lè)美學(xué)通論》 上海音樂(lè)出版社
【3】夏野:《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簡(jiǎn)編》 上海音樂(lè)出版社
【4】楊蔭瀏:《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稿》 人民音樂(lè)出版社
第2篇
[論文內(nèi)容提要]文章從倫理學(xué)的角度,對(duì)先秦儒家、道家音樂(lè)思想在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形成、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和深遠(yuǎn)影響做出了簡(jiǎn)潔明了的歸納和總結(jié),并闡明先秦音樂(lè)思想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甚至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聯(lián)系。
先秦時(shí)期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時(shí)期,作為倫理學(xué)的“德”的觀念發(fā)韌于夏代,中經(jīng)殷周和春秋戰(zhàn)國(guó),包含著豐富的內(nèi)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上有著重大影響的時(shí)期。由于這種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在對(duì)音樂(lè)文化的闡釋中,先秦音樂(lè)思想凸顯了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深厚的倫理意蘊(yùn)。
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中,“德”具有總攝諸體、兼收并蓄的意義及功能。尤其作為中國(guó)音樂(lè)思想中一個(gè)最為重要、最核心的觀念,從先秦典籍《論語(yǔ)》、《左傳》到漢代《禮記·樂(lè)記》,從戰(zhàn)國(guó)末期孟子、荀子的《樂(lè)論》到魏晉秘康的《聲無(wú)哀樂(lè)論》,以迄于唐、宋、元、明、清,歷代樂(lè)論、筆記、詩(shī)詞、小說(shuō)、曲論、唱論,無(wú)不浸潤(rùn)著“德”的觀念。謹(jǐn)遵道德規(guī)范,乃是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倫理、政治、美感和形態(tài)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時(shí)期的音樂(lè)倫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中,倫理精神與音樂(lè)藝術(shù)之間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國(guó)傳統(tǒng)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種藝術(shù)的境界,傳統(tǒng)藝術(shù)又在潛移默化中促進(jìn)人格的完成。先秦時(shí)期思想家學(xué)派繁多,在思想領(lǐng)域中產(chǎn)生了諸子蜂起、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成就了中國(guó)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頁(yè)。先秦典籍、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獻(xiàn)(包括出土的文獻(xiàn)如“簡(jiǎn)犢”“帛書(shū)”及“銘文”等)、文物實(shí)物資料是研究先秦音樂(lè)思想史料的主要來(lái)源。這些文獻(xiàn)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論語(yǔ)》,孟子、荀子的《樂(lè)論》及《周易》“象”,《周豐山“春官宗伯·大司樂(lè)”,《尚書(shū)》“堯典”、“皋陶漠”,《禮記》等經(jīng)典;墨家的墨子《三辯》、《非樂(lè)上》、《非儒樸和《公孟》;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商鞍《商君書(shū)》、韓非子;雜家的《管子》、《呂氏春秋》、《列子》、《國(guó)語(yǔ)》、《左嘟(先秦史書(shū));以及漢代的《史記》 ,《樂(lè)記》(后人記載的先秦歷史資料)等均載有一定的論樂(lè)文字。
第一個(gè)提出較系統(tǒng)的作為倫理學(xué)道德學(xué)說(shuō)的是春秋時(shí)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開(kāi)創(chuàng)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學(xué)說(shuō)的學(xué)派被稱(chēng)為“顯學(xué)”;以孔子為宗師,孟子和荀子繼承和發(fā)展的儒家學(xué)派建立了一個(gè)以“仁”“和”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現(xiàn);墨家學(xué)派的開(kāi)創(chuàng)者是墨翟,與儒家并稱(chēng)為“顯學(xué)”,他們興起聆儒家學(xué)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觀點(diǎn)與儒家學(xué)派針?shù)h相對(duì),是儒家的反對(duì)派。在文藝生活中,墨家認(rèn)為藝術(shù)的美與道德的善是應(yīng)當(dāng)統(tǒng)一的,違背道德的娛樂(lè)享受應(yīng)該禁止:法家音樂(lè)倫理思想出現(xiàn)于先秦,以商較和韓非為主要代表,其核心觀點(diǎn)是“不務(wù)德而務(wù)法”,片面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作用,否認(rèn)了道德的社會(huì)作用。盡管法家的“法治”理論并未被完全拋棄,但其“不務(wù)德而務(wù)法”的原則在以后的封建社會(huì)中被否定,因此對(duì)后世并無(wú)顯著影響。孔子及其前的音樂(lè)思想是儒道兩家音樂(lè)思想的共同源頭,以老子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現(xiàn)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評(píng)儒半的一個(gè)學(xué)派,老子和莊子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樂(lè)倫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時(shí)期豐富多樣的音樂(lè)生活中,產(chǎn)生了許多很有價(jià)值、影響至今的音樂(lè)理論思想。諸子就音樂(lè)倫理思想的論述相互對(duì)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這種“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堪稱(chēng)音樂(lè)史上思想繁榮的鼎盛時(shí)代。因?yàn)榉饨ㄖ髁x宗法等級(jí)統(tǒng)治的需要,儒道兩家思想貫穿了2000多年中國(guó)發(fā)展史,稱(chēng)為這個(gè)渙映大國(guó)數(shù)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響于后世,其重要性遠(yuǎn)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對(duì)儒家音樂(lè)思想的倫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里,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內(nèi)涵著濃厚的倫理道德意識(shí),儒家文化傳統(tǒng)是建筑在倫理道德的基礎(chǔ)上,“仁”成為中國(guó)哲學(xué)所關(guān)注的中心課題,于是,在認(rèn)同音樂(lè)給予人的快樂(lè)的同時(shí),將它與“仁”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的美與倫理道德的“仁”相統(tǒng)一。因此儒家音樂(lè)思想的價(jià)值取向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在音樂(lè)中極力表現(xiàn)對(duì)人的重視和以人為中心,這些特點(diǎn)吸引了許多文化學(xué)家的眼球,被他們視為一種人文主義文化,他們認(rèn)為在儒家音樂(lè)文化里,人的主體性是完全與倫理道德結(jié)合在一起的。因此音樂(lè)作品的創(chuàng)作也從“仁”出發(fā),為“仁”服務(wù);“正樂(lè)”、“靡靡之音”、“鄭衛(wèi)之音”等術(shù)語(yǔ)亦可以不加解釋的用于音樂(lè)批評(píng),并分別指稱(chēng)處于不同倫理地位的音樂(lè)。
儒家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強(qiáng)調(diào)禮樂(lè)一體,認(rèn)為音樂(lè)與倫理相通,所謂“禮者為同,樂(lè)者為異。同者相親,異則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學(xué)問(wèn)”,由于這種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中國(guó)音樂(lè)教育歷來(lái)主張以“德為美”。《周禮·春官宗伯》說(shuō):“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孔子曾有“興于詩(shī),立于禮,成于樂(l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è)何?”之言。孟子《公孫丑上》說(shuō):“聞其樂(lè)而知其德,’,這些言語(yǔ)都將音樂(lè)與仁德聯(lián)系起來(lái)。“德生禮,禮生樂(lè)”,從“德”到“禮”、“樂(lè)”,是一個(gè)自然生成的過(guò)程,禮樂(lè)被儒家視為德的表征。“六藝”是西周時(shí)期學(xué)校教育的六門(mén)課程,包括“禮”“樂(lè)”“射”“御”“書(shū)”“數(shù)”。其中禮:包括政治、歷史和以“孝”為根本的倫理道德教育。樂(lè)屬于綜合藝術(shù),包括音樂(lè)、詩(shī)歌和舞蹈。其中,禮樂(lè)代表西周的意識(shí)形態(tài),是決定教育的貴族性質(zhì)的因素。樂(lè)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禮進(jìn)行倫理道德教育,禮重點(diǎn)在于約束子弟們外表的行為,樂(lè)重點(diǎn)在于調(diào)和子弟們內(nèi)在的感情。
孔子開(kāi)創(chuàng)了儒家的音樂(lè)倫理理論,建立起情感與倫理道德、個(gè)人與社會(huì)和諧的音樂(lè)思想,影響了整個(gè)封建時(shí)代音樂(lè)思想的發(fā)展,使中國(guó)古代思想進(jìn)入了一個(gè)輝煌的時(shí)期。這些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yǔ)》中都有具體體現(xiàn)。第一:“樂(lè)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樂(lè)從道德上感化人。“文質(zhì)彬彬”是孔子的審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個(gè)人要注重禮樂(lè)即音樂(lè)文化修養(yǎng);“質(zhì)”即實(shí)質(zhì),指一個(gè)人的仁義之道及倫理品德。孔子認(rèn)為:一個(gè)人沒(méi)有禮樂(lè)修養(yǎng)就顯得氣質(zhì)不佳,但只有禮樂(lè)修養(yǎng)而缺乏仁義之道的倫理品德便是一種虛飾;所以他還說(shuō)“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異,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強(qiáng)調(diào)具有禮樂(lè)修養(yǎng)與仁義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發(fā)展才是文質(zhì)協(xié)調(diào)。第二:“道德之內(nèi)涵在仁”—即音樂(lè)要貫注“仁”的道德內(nèi)涵,孔子認(rèn)為“樂(lè)”可以感化人的心靈,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仁義禮道,從而發(fā)展為君子。孔子說(shuō):“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è)何?”意思是說(shuō):人如果沒(méi)有仁愛(ài),講什么禮?人如果沒(méi)有仁愛(ài),講什么樂(lè)?說(shuō)的是外在形式的禮樂(lè),都應(yīng)以?xún)?nèi)在心理情感為真正的憑依,否則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見(jiàn),孔子的觀點(diǎn)非常明確:禮樂(lè)的本質(zhì)是“仁”,為人“不仁”,便無(wú)從對(duì)待禮樂(lè)。孔子在哲學(xué)上崇尚中庸之道,藝術(shù)上提倡中和之美淚而胃的“樂(lè)而不,哀而不傷”將中庸之道運(yùn)用于音樂(lè)并將情感的因素統(tǒng)一起來(lái),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殺另一因素的片面性,這無(wú)疑是符合音樂(lè)藝術(shù)的內(nèi)在規(guī)律。 第三:“盡善盡美的和諧”—即音樂(lè)形式與內(nèi)容、情感與道德的統(tǒng)一。孔子認(rèn)為音樂(lè)有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他評(píng)價(jià)音樂(lè)的標(biāo)準(zhǔn)是“善”和“美”。所謂“善”是指內(nèi)容的完善,“美”是指音樂(lè)的形式美好、動(dòng)聽(tīng);二者能完美結(jié)合就盡善盡美了。這就將音樂(lè)的內(nèi)容與形式和“禮”、“仁愛(ài)”結(jié)合起來(lái)了。他在齊國(guó)觀聽(tīng)古樂(lè)舞《韶》后,認(rèn)為獲得了一次很高的藝術(shù)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說(shuō):“不圖為樂(lè)之至于斯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但接著評(píng)價(jià)另一部古典樂(lè)舞《武》時(shí)卻說(shuō):“盡美矣,未盡善也!”可見(jiàn)他推崇《韶》,并要求樂(lè)應(yīng)合乎禮的規(guī)范。他斷言,歌頌舜帝功德的《韶》樂(lè)的內(nèi)容和形式都達(dá)到了高度統(tǒng)一。而《武》這部反映武王滅商興周事跡的樂(lè)舞,雖欣賞起來(lái)很美,但過(guò)多表現(xiàn)征伐的武力行為,未能完全做到仁愛(ài),所以“未盡善也”。而《韶》樂(lè)則是贊頌舜帝德治的內(nèi)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因此,孔子在正樂(lè)時(shí)說(shuō):“樂(lè)則韶舞、放鄭聲、遠(yuǎn)佞人;鄭聲,佞人殆”。將符合他思想的《韶》樂(lè)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作為音樂(lè)舞蹈的判斷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容與形式、情感與道德的統(tǒng)一。孔子的“盡善盡美”的主張是對(duì)古代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是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特征的認(rèn)識(shí)和審美評(píng)價(jià)的一次飛躍。,孔子對(duì)音樂(lè)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非常清楚地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審美與情感及道德相結(jié)合。故歷來(lái)的儒家音樂(lè)既維護(hù)“禮”,又滿(mǎn)足感官的愉悅。使教育通過(guò)藝術(shù)表現(xiàn)出來(lái),人的情感在正常發(fā)泄時(shí)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與道德的升華,教育也通過(guò)審美而獲得體現(xiàn);即所謂的“寓教于樂(lè)”;從而形成了儒家的“樂(lè)感文化”。
儒家用詩(shī)繼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倫理的傳統(tǒng),孔子對(duì)《詩(shī)經(jīng)》的闡釋?zhuān)王r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詩(shī)經(jīng)》是西周樂(lè)官文化的產(chǎn)物。從藝術(shù)功用上看,《詩(shī)經(jīng)》體現(xiàn)了以德為本、以禮為用的文化價(jià)值和鮮明的理性精神。“德”是樂(lè)官必備的素質(zhì),“樂(lè)德”是貴族音樂(lè)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學(xué)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理論范疇。《詩(shī)經(jīng)》依據(jù)塑造倫理人格、完善群體道德的理想,描寫(xiě)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風(fēng),贊美了等級(jí)社會(huì)宗子宗孫、世卿世祿的宗法制度,個(gè)體則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組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之中,而鮮有個(gè)性的表現(xiàn)。因此《詩(shī)經(jīng)》堪稱(chēng)西周禮樂(lè)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藝術(shù)與文化的深層聯(lián)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發(fā)德也歌者在上,鮑竹在下,貴人聲也。”《禮記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所謂“登歌”、“升歌”,皆為人聲之歌,而樂(lè)器多半處于從屬地位。周人“貴人聲”,顯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視樂(lè)歌所激發(fā)的道德倫理情感(“發(fā)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為樂(lè)之本”、“德音之謂樂(lè)”之說(shuō)。《詩(shī)經(jīng)》雅、頌兩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著這類(lèi)“德”的說(shuō)教和“德音”的頌美之辭,與《國(guó)風(fēng)》中的那些清新活潑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風(fēng)格,同時(shí)為儒家的倫理政治學(xué)說(shuō)提供了最豐富最現(xiàn)成的思想資料。由此可見(jiàn),儒家的言必稱(chēng)《詩(shī)》、《書(shū)》,行必?fù)?jù)《禮》、《樂(lè)》,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禮樂(lè)文明中,樂(lè)體現(xiàn)出深厚的倫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對(duì)道家音樂(lè)思想的倫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國(guó)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辯哲學(xué),也是一派實(shí)際可用的關(guān)于如何處理人際關(guān)系、如何達(dá)到福樂(lè)人生的倫理學(xué)。道家倫理體系,也以其恢宏的規(guī)模、納米般的邏輯,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歷程中社會(huì)和文化所帶來(lái)的鐵一般的證據(jù),鑄造了它的以“宇宙主義”為理論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為特點(diǎn)的倫理學(xué)體系。這樣一種倫理學(xué),發(fā)人之所未發(fā),道人之所未道,其在倫理學(xué)理論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思考和對(duì)社會(huì)不合理現(xiàn)象的批判,至今都是發(fā)人深省的。老莊及其弟子和諸多道學(xué)的后繼者通過(guò)對(duì)“社會(huì)倫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達(dá)了他們重自然的天理倫理觀。他們的音樂(lè)思想也含有豐富的自然主義倫理觀。
道家對(duì)藝術(shù)審美和藝術(shù)所具有的特征有著深刻的認(rèn)識(shí),它高度重視人的理性精神,但反對(duì)用特定的社會(huì)倫理道德來(lái)規(guī)范人的情感。它主張自然、無(wú)為,強(qiáng)調(diào)情感的自由抒發(fā)和表現(xiàn)。老子認(rèn)為,理想的音樂(lè)是“大音希聲”,是合乎道之特性的無(wú)聲之樂(lè),是白然、恬淡、用之不盡的至美之樂(lè)。有聲之樂(lè)或“五音”則是不合乎道之特性的不完美的音樂(lè);老子甚至告誡道:“五音令人耳聾”。莊子繼承了這一思想,并進(jìn)一步闡明,合乎“道”的音樂(lè)是“天”、“真”之樂(lè),是自然之樂(lè);唯它才具備音樂(lè)之“和”(即精神內(nèi)涵);而這“和”才是音樂(lè)中最內(nèi)在、最本質(zhì)的東西,才是音樂(lè)之至美所在。簡(jiǎn)言之,自然之樂(lè)是“充滿(mǎn)天地,苞裹六極”的宇宙之樂(lè)。老子否定一切人為的有聲之樂(lè),推崇“大音希聲”,強(qiáng)調(diào)恬淡而不可欲,其意義是消極的:莊子則要以追求“天籟”似的自然之樂(lè)、宇宙之樂(lè),來(lái)反對(duì)一切束縛人心、扭曲人性的有聲之樂(lè),與此同時(shí),又肯定合乎人的自然之情性的有聲之樂(lè),因此,其意義是積極的。老莊道家音樂(lè)倫理思想,經(jīng)過(guò)《淮南子》以及稽康、李蟄等人,獲得進(jìn)一步發(fā)展。稽康音樂(lè)思想的倫理觀是道家音樂(lè)思想精髓在魏晉時(shí)期放射出的一道驚世駭俗的異彩。稽康在遵循道家自然主義音樂(lè)倫理思想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聲無(wú)哀樂(lè)論”的命題,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儒家“音由心生”、“樂(lè)與政通”、“樂(lè)通倫理”的音樂(lè)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chǔ)。稽康認(rèn)為,天地產(chǎn)生萬(wàn)物,音樂(lè)是萬(wàn)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之“氣”所生,因而,音樂(lè)獨(dú)立于天地之間,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與人的哀樂(lè)無(wú)關(guān)。換句話(huà)說(shuō),音樂(lè)是客觀的存在,哀樂(lè)則是主觀的東西,二者互不相干,音樂(lè)不包含哀樂(lè),也不能喚起相應(yīng)的哀樂(lè)。此所謂“外內(nèi)殊用,彼我異名”;“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jīng)緯”。顯而易見(jiàn)稽康明確割斷了音樂(lè)與心(情感)之間的聯(lián)系。彰顯了其崇尚自由、重自由的天理倫理觀。
第3篇
[論文內(nèi)容提要]文章從倫理學(xué)的角度,對(duì)先秦儒家、道家音樂(lè)思想在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形成、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和深遠(yuǎn)影響做出了簡(jiǎn)潔明了的歸納和總結(jié),并闡明先秦音樂(lè)思想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甚至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聯(lián)系。
先秦時(shí)期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時(shí)期,作為倫理學(xué)的“德”的觀念發(fā)韌于夏代,中經(jīng)殷周和春秋戰(zhàn)國(guó),包含著豐富的內(nèi)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思想上有著重大影響的時(shí)期。由于這種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在對(duì)音樂(lè)文化的闡釋中,先秦音樂(lè)思想凸顯了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深厚的倫理意蘊(yùn)。
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中,“德”具有總攝諸體、兼收并蓄的意義及功能。尤其作為中國(guó)音樂(lè)思想中一個(gè)最為重要、最核心的觀念,從先秦典籍《論語(yǔ)》、《左傳》到漢代《禮記·樂(lè)記》,從戰(zhàn)國(guó)末期孟子、荀子的《樂(lè)論》到魏晉秘康的《聲無(wú)哀樂(lè)論》,以迄于唐、宋、元、明、清,歷代樂(lè)論、筆記、詩(shī)詞、小說(shuō)、曲論、唱論,無(wú)不浸潤(rùn)著“德”的觀念。謹(jǐn)遵道德規(guī)范,乃是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倫理、政治、美感和形態(tài)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時(shí)期的音樂(lè)倫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中,倫理精神與音樂(lè)藝術(shù)之間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國(guó)傳統(tǒng)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種藝術(shù)的境界,傳統(tǒng)藝術(shù)又在潛移默化中促進(jìn)人格的完成。先秦時(shí)期思想家學(xué)派繁多,在思想領(lǐng)域中產(chǎn)生了諸子蜂起、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成就了中國(guó)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頁(yè)。先秦典籍、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獻(xiàn)(包括出土的文獻(xiàn)如“簡(jiǎn)犢”“帛書(shū)”及“銘文”等)、文物實(shí)物資料是研究先秦音樂(lè)思想史料的主要來(lái)源。這些文獻(xiàn)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論語(yǔ)》,孟子、荀子的《樂(lè)論》及《周易》“象”,《周豐山“春官宗伯·大司樂(lè)”,《尚書(shū)》“堯典”、“皋陶漠”,《禮記》等經(jīng)典;墨家的墨子《三辯》、《非樂(lè)上》、《非儒樸和《公孟》;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商鞍《商君書(shū)》、韓非子;雜家的《管子》、《呂氏春秋》、《列子》、《國(guó)語(yǔ)》、《左嘟(先秦史書(shū));以及漢代的《史記》,《樂(lè)記》(后人記載的先秦歷史資料)等均載有一定的論樂(lè)文字。
第一個(gè)提出較系統(tǒng)的作為倫理學(xué)道德學(xué)說(shuō)的是春秋時(shí)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開(kāi)創(chuàng)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學(xué)說(shuō)的學(xué)派被稱(chēng)為“顯學(xué)”;以孔子為宗師,孟子和荀子繼承和發(fā)展的儒家學(xué)派建立了一個(gè)以“仁”“和”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現(xiàn);墨家學(xué)派的開(kāi)創(chuàng)者是墨翟,與儒家并稱(chēng)為“顯學(xué)”,他們興起聆儒家學(xué)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觀點(diǎn)與儒家學(xué)派針?shù)h相對(duì),是儒家的反對(duì)派。在文藝生活中,墨家認(rèn)為藝術(shù)的美與道德的善是應(yīng)當(dāng)統(tǒng)一的,違背道德的娛樂(lè)享受應(yīng)該禁止:法家音樂(lè)倫理思想出現(xiàn)于先秦,以商較和韓非為主要代表,其核心觀點(diǎn)是“不務(wù)德而務(wù)法”,片面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作用,否認(rèn)了道德的社會(huì)作用。盡管法家的“法治”理論并未被完全拋棄,但其“不務(wù)德而務(wù)法”的原則在以后的封建社會(huì)中被否定,因此對(duì)后世并無(wú)顯著影響。孔子及其前的音樂(lè)思想是儒道兩家音樂(lè)思想的共同源頭,以老子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現(xiàn)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評(píng)儒半的一個(gè)學(xué)派,老子和莊子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樂(lè)倫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時(shí)期豐富多樣的音樂(lè)生活中,產(chǎn)生了許多很有價(jià)值、影響至今的音樂(lè)理論思想。諸子就音樂(lè)倫理思想的論述相互對(duì)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這種“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堪稱(chēng)音樂(lè)史上思想繁榮的鼎盛時(shí)代。因?yàn)榉饨ㄖ髁x宗法等級(jí)統(tǒng)治的需要,儒道兩家思想貫穿了2000多年中國(guó)發(fā)展史,稱(chēng)為這個(gè)渙映大國(guó)數(shù)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響于后世,其重要性遠(yuǎn)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對(duì)儒家音樂(lè)思想的倫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里,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內(nèi)涵著濃厚的倫理道德意識(shí),儒家文化傳統(tǒng)是建筑在倫理道德的基礎(chǔ)上,“仁”成為中國(guó)哲學(xué)所關(guān)注的中心課題,于是,在認(rèn)同音樂(lè)給予人的快樂(lè)的同時(shí),將它與“仁”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的美與倫理道德的“仁”相統(tǒng)一。因此儒家音樂(lè)思想的價(jià)值取向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在音樂(lè)中極力表現(xiàn)對(duì)人的重視和以人為中心,這些特點(diǎn)吸引了許多文化學(xué)家的眼球,被他們視為一種人文主義文化,他們認(rèn)為在儒家音樂(lè)文化里,人的主體性是完全與倫理道德結(jié)合在一起的。因此音樂(lè)作品的創(chuàng)作也從“仁”出發(fā),為“仁”服務(wù);“正樂(lè)”、“靡靡之音”、“鄭衛(wèi)之音”等術(shù)語(yǔ)亦可以不加解釋的用于音樂(lè)批評(píng),并分別指稱(chēng)處于不同倫理地位的音樂(lè)。
儒家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強(qiáng)調(diào)禮樂(lè)一體,認(rèn)為音樂(lè)與倫理相通,所謂“禮者為同,樂(lè)者為異。同者相親,異則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學(xué)問(wèn)”,由于這種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中國(guó)音樂(lè)教育歷來(lái)主張以“德為美”。《周禮·春官宗伯》說(shuō):“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孔子曾有“興于詩(shī),立于禮,成于樂(l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è)何?”之言。孟子《公孫丑上》說(shuō):“聞其樂(lè)而知其德,’,這些言語(yǔ)都將音樂(lè)與仁德聯(lián)系起來(lái)。“德生禮,禮生樂(lè)”,從“德”到“禮”、“樂(lè)”,是一個(gè)自然生成的過(guò)程,禮樂(lè)被儒家視為德的表征。“六藝”是西周時(shí)期學(xué)校教育的六門(mén)課程,包括“禮”“樂(lè)”“射”“御”“書(shū)”“數(shù)”。其中禮:包括政治、歷史和以“孝”為根本的倫理道德教育。樂(lè)屬于綜合藝術(shù),包括音樂(lè)、詩(shī)歌和舞蹈。其中,禮樂(lè)代表西周的意識(shí)形態(tài),是決定教育的貴族性質(zhì)的因素。樂(lè)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禮進(jìn)行倫理道德教育,禮重點(diǎn)在于約束子弟們外表的行為,樂(lè)重點(diǎn)在于調(diào)和子弟們內(nèi)在的感情。
孔子開(kāi)創(chuàng)了儒家的音樂(lè)倫理理論,建立起情感與倫理道德、個(gè)人與社會(huì)和諧的音樂(lè)思想,影響了整個(gè)封建時(shí)代音樂(lè)思想的發(fā)展,使中國(guó)古代思想進(jìn)入了一個(gè)輝煌的時(shí)期。這些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yǔ)》中都有具體體現(xiàn)。第一:“樂(lè)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樂(lè)從道德上感化人。“文質(zhì)彬彬”是孔子的審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個(gè)人要注重禮樂(lè)即音樂(lè)文化修養(yǎng);“質(zhì)”即實(shí)質(zhì),指一個(gè)人的仁義之道及倫理品德。孔子認(rèn)為:一個(gè)人沒(méi)有禮樂(lè)修養(yǎng)就顯得氣質(zhì)不佳,但只有禮樂(lè)修養(yǎng)而缺乏仁義之道的倫理品德便是一種虛飾;所以他還說(shuō)“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異,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強(qiáng)調(diào)具有禮樂(lè)修養(yǎng)與仁義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發(fā)展才是文質(zhì)協(xié)調(diào)。第二:“道德之內(nèi)涵在仁”—即音樂(lè)要貫注“仁”的道德內(nèi)涵,孔子認(rèn)為“樂(lè)”可以感化人的心靈,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仁義禮道,從而發(fā)展為君子。孔子說(shuō):“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è)何?”意思是說(shuō):人如果沒(méi)有仁愛(ài),講什么禮?人如果沒(méi)有仁愛(ài),講什么樂(lè)?說(shuō)的是外在形式的禮樂(lè),都應(yīng)以?xún)?nèi)在心理情感為真正的憑依,否則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見(jiàn),孔子的觀點(diǎn)非常明確:禮樂(lè)的本質(zhì)是“仁”,為人“不仁”,便無(wú)從對(duì)待禮樂(lè)。孔子在哲學(xué)上崇尚中庸之道,藝術(shù)上提倡中和之美淚而胃的“樂(lè)而不,哀而不傷”將中庸之道運(yùn)用于音樂(lè)并將情感的因素統(tǒng)一起來(lái),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殺另一因素的片面性,這無(wú)疑是符合音樂(lè)藝術(shù)的內(nèi)在規(guī)律。第三:“盡善盡美的和諧”—即音樂(lè)形式與內(nèi)容、情感與道德的統(tǒng)一。孔子認(rèn)為音樂(lè)有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他評(píng)價(jià)音樂(lè)的標(biāo)準(zhǔn)是“善”和“美”。所謂“善”是指內(nèi)容的完善,“美”是指音樂(lè)的形式美好、動(dòng)聽(tīng);二者能完美結(jié)合就盡善盡美了。這就將音樂(lè)的內(nèi)容與形式和“禮”、“仁愛(ài)”結(jié)合起來(lái)了。他在齊國(guó)觀聽(tīng)古樂(lè)舞《韶》后,認(rèn)為獲得了一次很高的藝術(shù)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說(shuō):“不圖為樂(lè)之至于斯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但接著評(píng)價(jià)另一部古典樂(lè)舞《武》時(shí)卻說(shuō):“盡美矣,未盡善也!”可見(jiàn)他推崇《韶》,并要求樂(lè)應(yīng)合乎禮的規(guī)范。他斷言,歌頌舜帝功德的《韶》樂(lè)的內(nèi)容和形式都達(dá)到了高度統(tǒng)一。而《武》這部反映武王滅商興周事跡的樂(lè)舞,雖欣賞起來(lái)很美,但過(guò)多表現(xiàn)征伐的武力行為,未能完全做到仁愛(ài),所以“未盡善也”。而《韶》樂(lè)則是贊頌舜帝德治的內(nèi)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因此,孔子在正樂(lè)時(shí)說(shuō):“樂(lè)則韶舞、放鄭聲、遠(yuǎn)佞人;鄭聲,佞人殆”。將符合他思想的《韶》樂(lè)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作為音樂(lè)舞蹈的判斷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容與形式、情感與道德的統(tǒng)一。孔子的“盡善盡美”的主張是對(duì)古代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是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特征的認(rèn)識(shí)和審美評(píng)價(jià)的一次飛躍。,孔子對(duì)音樂(lè)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非常清楚地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審美與情感及道德相結(jié)合。故歷來(lái)的儒家音樂(lè)既維護(hù)“禮”,又滿(mǎn)足感官的愉悅。使教育通過(guò)藝術(shù)表現(xiàn)出來(lái),人的情感在正常發(fā)泄時(shí)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與道德的升華,教育也通過(guò)審美而獲得體現(xiàn);即所謂的“寓教于樂(lè)”;從而形成了儒家的“樂(lè)感文化”。
儒家用詩(shī)繼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倫理的傳統(tǒng),孔子對(duì)《詩(shī)經(jīng)》的闡釋?zhuān)王r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詩(shī)經(jīng)》是西周樂(lè)官文化的產(chǎn)物。從藝術(shù)功用上看,《詩(shī)經(jīng)》體現(xiàn)了以德為本、以禮為用的文化價(jià)值和鮮明的理性精神。“德”是樂(lè)官必備的素質(zhì),“樂(lè)德”是貴族音樂(lè)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學(xué)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理論范疇。《詩(shī)經(jīng)》依據(jù)塑造倫理人格、完善群體道德的理想,描寫(xiě)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風(fēng),贊美了等級(jí)社會(huì)宗子宗孫、世卿世祿的宗法制度,個(gè)體則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組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之中,而鮮有個(gè)性的表現(xiàn)。因此《詩(shī)經(jīng)》堪稱(chēng)西周禮樂(lè)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藝術(shù)與文化的深層聯(lián)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發(fā)德也歌者在上,鮑竹在下,貴人聲也。”《禮記·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所謂“登歌”、“升歌”,皆為人聲之歌,而樂(lè)器多半處于從屬地位。周人“貴人聲”,顯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視樂(lè)歌所激發(fā)的道德倫理情感(“發(fā)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為樂(lè)之本”、“德音之謂樂(lè)”之說(shuō)。《詩(shī)經(jīng)》雅、頌兩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著這類(lèi)“德”的說(shuō)教和“德音”的頌美之辭,與《國(guó)風(fēng)》中的那些清新活潑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風(fēng)格,同時(shí)為儒家的倫理政治學(xué)說(shuō)提供了最豐富最現(xiàn)成的思想資料。由此可見(jiàn),儒家的言必稱(chēng)《詩(shī)》、《書(shū)》,行必?fù)?jù)《禮》、《樂(lè)》,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禮樂(lè)文明中,樂(lè)體現(xiàn)出深厚的倫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對(duì)道家音樂(lè)思想的倫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國(guó)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辯哲學(xué),也是一派實(shí)際可用的關(guān)于如何處理人際關(guān)系、如何達(dá)到福樂(lè)人生的倫理學(xué)。道家倫理體系,也以其恢宏的規(guī)模、納米般的邏輯,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歷程中社會(huì)和文化所帶來(lái)的鐵一般的證據(jù),鑄造了它的以“宇宙主義”為理論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為特點(diǎn)的倫理學(xué)體系。這樣一種倫理學(xué),發(fā)人之所未發(fā),道人之所未道,其在倫理學(xué)理論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思考和對(duì)社會(huì)不合理現(xiàn)象的批判,至今都是發(fā)人深省的。老莊及其弟子和諸多道學(xué)的后繼者通過(guò)對(duì)“社會(huì)倫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達(dá)了他們重自然的天理倫理觀。他們的音樂(lè)思想也含有豐富的自然主義倫理觀。
道家對(duì)藝術(shù)審美和藝術(shù)所具有的特征有著深刻的認(rèn)識(shí),它高度重視人的理性精神,但反對(duì)用特定的社會(huì)倫理道德來(lái)規(guī)范人的情感。它主張自然、無(wú)為,強(qiáng)調(diào)情感的自由抒發(fā)和表現(xiàn)。老子認(rèn)為,理想的音樂(lè)是“大音希聲”,是合乎道之特性的無(wú)聲之樂(lè),是白然、恬淡、用之不盡的至美之樂(lè)。有聲之樂(lè)或“五音”則是不合乎道之特性的不完美的音樂(lè);老子甚至告誡道:“五音令人耳聾”。莊子繼承了這一思想,并進(jìn)一步闡明,合乎“道”的音樂(lè)是“天”、“真”之樂(lè),是自然之樂(lè);唯它才具備音樂(lè)之“和”(即精神內(nèi)涵);而這“和”才是音樂(lè)中最內(nèi)在、最本質(zhì)的東西,才是音樂(lè)之至美所在。簡(jiǎn)言之,自然之樂(lè)是“充滿(mǎn)天地,苞裹六極”的宇宙之樂(lè)。老子否定一切人為的有聲之樂(lè),推崇“大音希聲”,強(qiáng)調(diào)恬淡而不可欲,其意義是消極的:莊子則要以追求“天籟”似的自然之樂(lè)、宇宙之樂(lè),來(lái)反對(duì)一切束縛人心、扭曲人性的有聲之樂(lè),與此同時(shí),又肯定合乎人的自然之情性的有聲之樂(lè),因此,其意義是積極的。老莊道家音樂(lè)倫理思想,經(jīng)過(guò)《淮南子》以及稽康、李蟄等人,獲得進(jìn)一步發(fā)展。稽康音樂(lè)思想的倫理觀是道家音樂(lè)思想精髓在魏晉時(shí)期放射出的一道驚世駭俗的異彩。稽康在遵循道家自然主義音樂(lè)倫理思想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聲無(wú)哀樂(lè)論”的命題,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儒家“音由心生”、“樂(lè)與政通”、“樂(lè)通倫理”的音樂(lè)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chǔ)。稽康認(rèn)為,天地產(chǎn)生萬(wàn)物,音樂(lè)是萬(wàn)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之“氣”所生,因而,音樂(lè)獨(dú)立于天地之間,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與人的哀樂(lè)無(wú)關(guān)。換句話(huà)說(shuō),音樂(lè)是客觀的存在,哀樂(lè)則是主觀的東西,二者互不相干,音樂(lè)不包含哀樂(lè),也不能喚起相應(yīng)的哀樂(lè)。此所謂“外內(nèi)殊用,彼我異名”;“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jīng)緯”。顯而易見(jiàn)稽康明確割斷了音樂(lè)與心(情感)之間的聯(lián)系。彰顯了其崇尚自由、重自由的天理倫理觀。